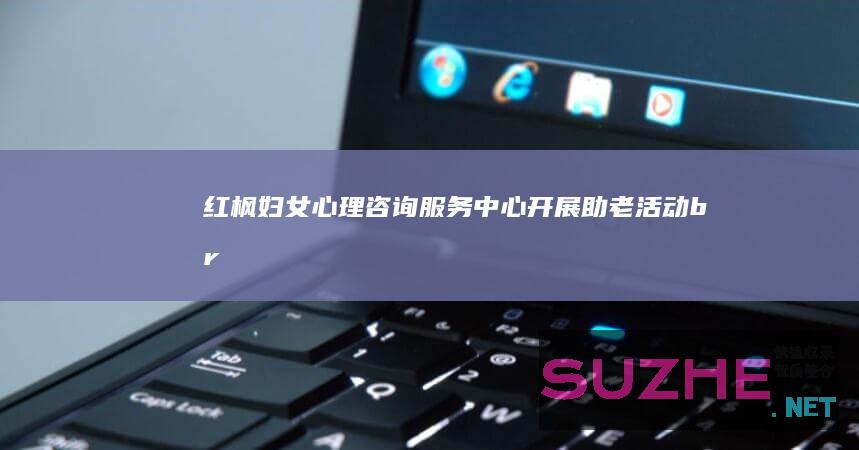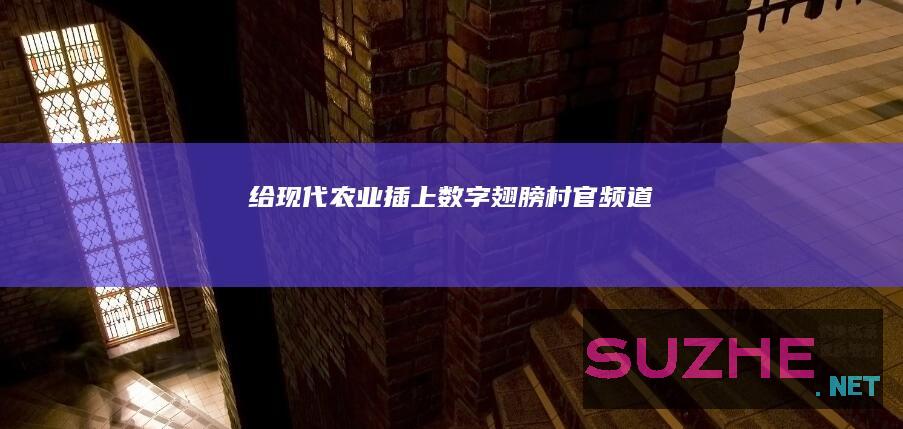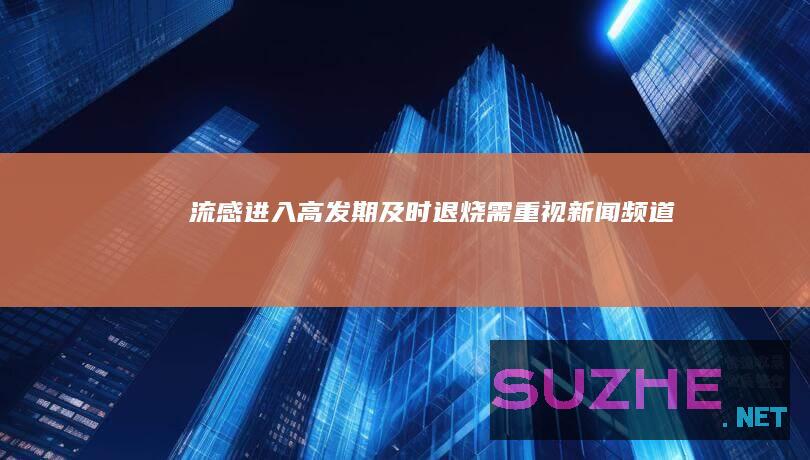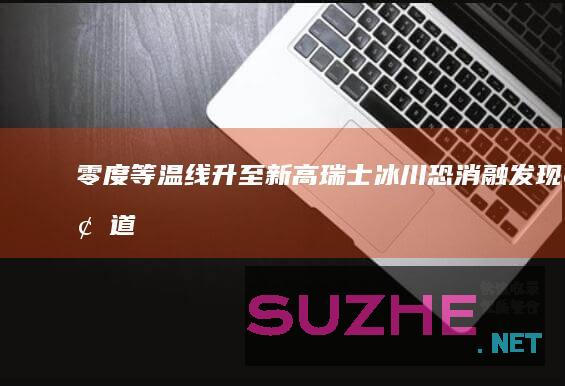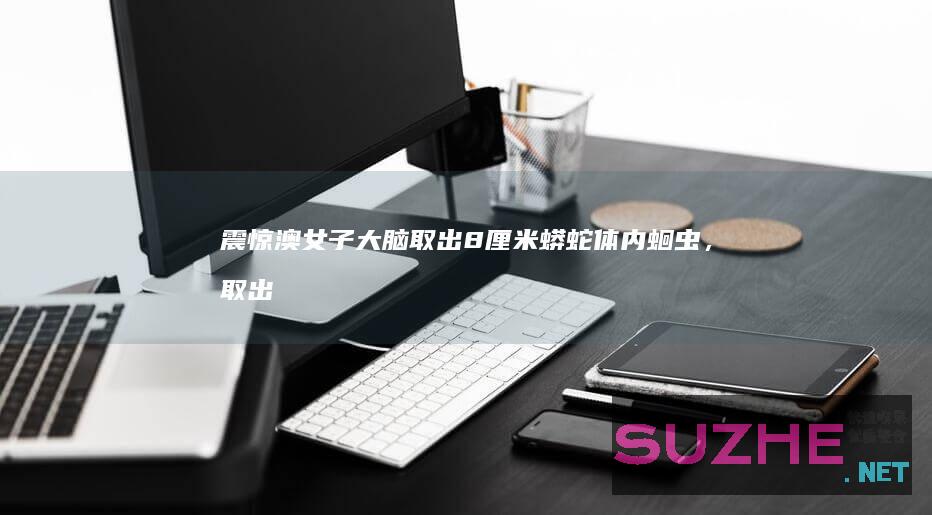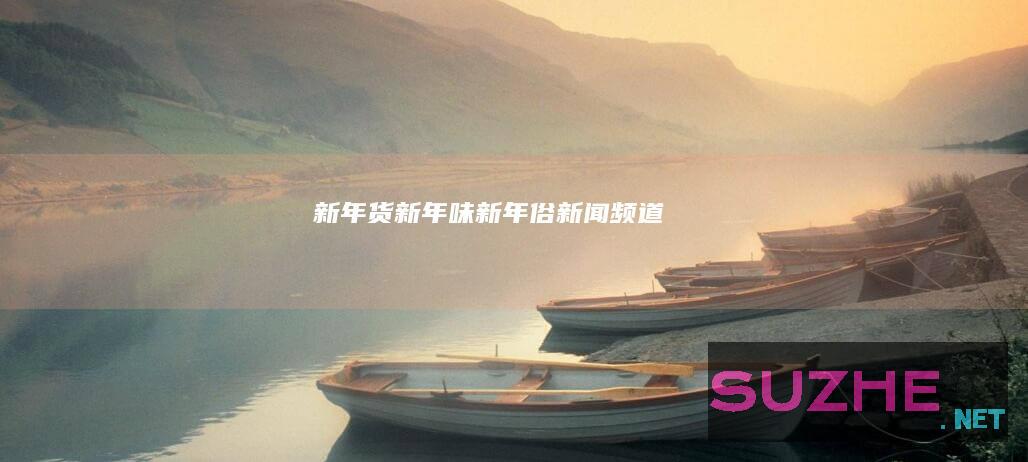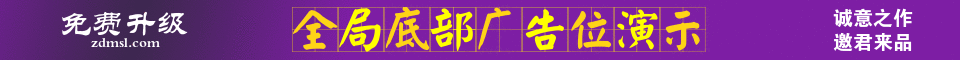钱理群:以“课堂实录”的形式,重返文学现场_新闻频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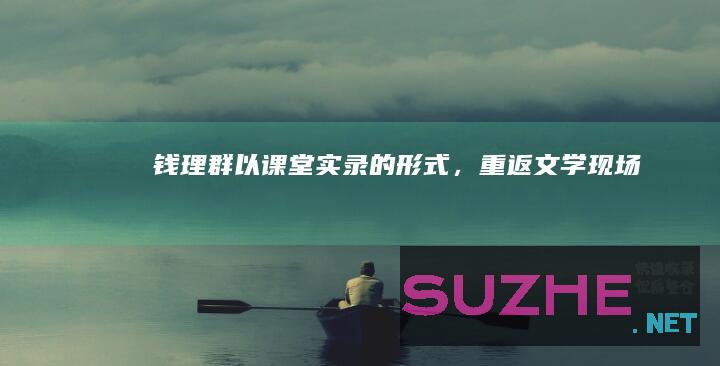
钱理群在图书分享会上。(左二为钱理群)图片由方所北京提供
“这是一次难能可贵的精神对话与学术漫游。”
《现代小说十家新读》是根据钱理群教授在北京大学1995年秋季学期开设的“40年代小说研读”课程内容“开箱”整理而来。30年后,当年亲历这次讨论课的北大中文系教授吴晓东领着新一代学子在前辈的光环下重释这些作品,加入了现代文学专业在读研究生新的解读文字,贡献了新的方法论视野,可谓两代中文系学人对“40年代小说研读”的课堂实录。
书中选取萧红、李拓之、沈从文、端木蕻良、路翎、冯至、废名、卞之琳、张爱玲、汪曾祺10位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作家作品及学术研究,从萧红《后花园》对人的存在的探讨,到张爱玲《封锁》是否“意义过溢”,再到汪曾祺《异秉》新旧两种版本的对读……以课堂实录、师生平等交流的形式,重返文学现场。
“多少摆脱了功利性的求知和探索的精神”
钱理群表示,这些对话整理成书后,又形成了3层结构。“先是‘领读者言’,即老师的总体导游,再是‘众生喧哗’,是老师与全体学生参与的课堂讨论。每一次由一个学生作报告,然后集体讨论,最后由老师作点评。最后一节是‘纵横评说’,在微观研究的基础上,由老师提升到文学史的大视野和高度作宏观的上世纪40年代小说的历史地位与总体结构的论述。”
钱理群说:“在我心目中,‘教师’的地位高于也重于‘学术研究’。我也深深感怀于那一代研究生们对学术所葆有的单纯的热情,以及多少摆脱了功利性的求知和探索的精神。”
北大中文系教授、《现代小说十家新读》的另一位主编吴晓东,20年前还是留校不久的“青年教师”,当时全程旁听了钱理群老师的“40年代小说研读”课,他坦言,“那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经历”。
吴晓东说:“个人觉得在我的教课生涯中,最难的是1995年的秋天,我已经当了一年多的青年教师,但是还没有适应这个角色,经常为怎么教课发愁。钱老师这门讨论课对我来说是及时雨,也奠定了我后来自己上讨论课的一个基本方法。”
加入了新一代青年学者的“再研读”
吴晓东将钱理群老师的“对话与漫游”形式沿用到了2020年及之后的北大课堂,当时,钱理群教授在课堂上研读的作品逐渐完成了经典化后,吴晓东老师将新的课程命名为“40年代小说经典研读”。《现代小说十家新读》一书中,也加入了新一代青年学者的“再研读”。
孙慈姗说:“我们看到了师长和前辈们对我们的鼓励、关怀和引导,看到了同伴们的相互扶持,也感受到了学院内外发生的互动和思想情感的激荡。就像作家的心态要在文本形式中显影,那所谓的薪火相传、学术传承、彼此照亮的美好的想象,也需要被具象化。”
“在我的研究重心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转向思想史、精神史、政治史研究之前,我始终把自己认定为‘文学史家’。”钱理群说,“‘钱理群现代文学课’丛书背后有我的学术研究的‘三承担’意识,即‘对自我的承担,对社会和历史的承担,对学科发展的承担’。我曾经有意用夸张的语调写道:‘天生我材必有用,我就是为这个学科而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不能没有我钱理群。’这样的‘故作多情’其实就是一种历史的使命感。”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李浴洋是吴晓东和贺桂梅的学生,也是《现代小说十家新读》的学术统筹。黎启康是李浴洋的学生,作为00后新一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上述学者的论文著作成为他日常研究的重要参考,文学研究以“四代同台”的形式传承着。
吴晓东说:“钱老师希望学生能通过对作家的经典作品进行研读,实现研究者(学生)自我的精神转化与升华。这门课程承担的是塑造研究者精神主体性的功能,形成多重的对话空间。学生们要有对作品在精神上的感悟,才能激发自己的想象力、创造力,激发对文学作品的开放式的理解,进而在学术漫游的一种愉悦和快乐中培养自己独立的研究能力。”
| |24小时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010-64098588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10120170007号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A2.B1-20232628/京B2-20224905号|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0105108号
相关标签: 钱理群;文学史家;文学形式、
本文地址:https://suzhe.net/article/ce1fcb5ea31b048b9b8f.html
<a href="https://suzhe.net/" target="_blank">素著网- 快速收录,优质整合!</a>

 人气排行榜
人气排行榜